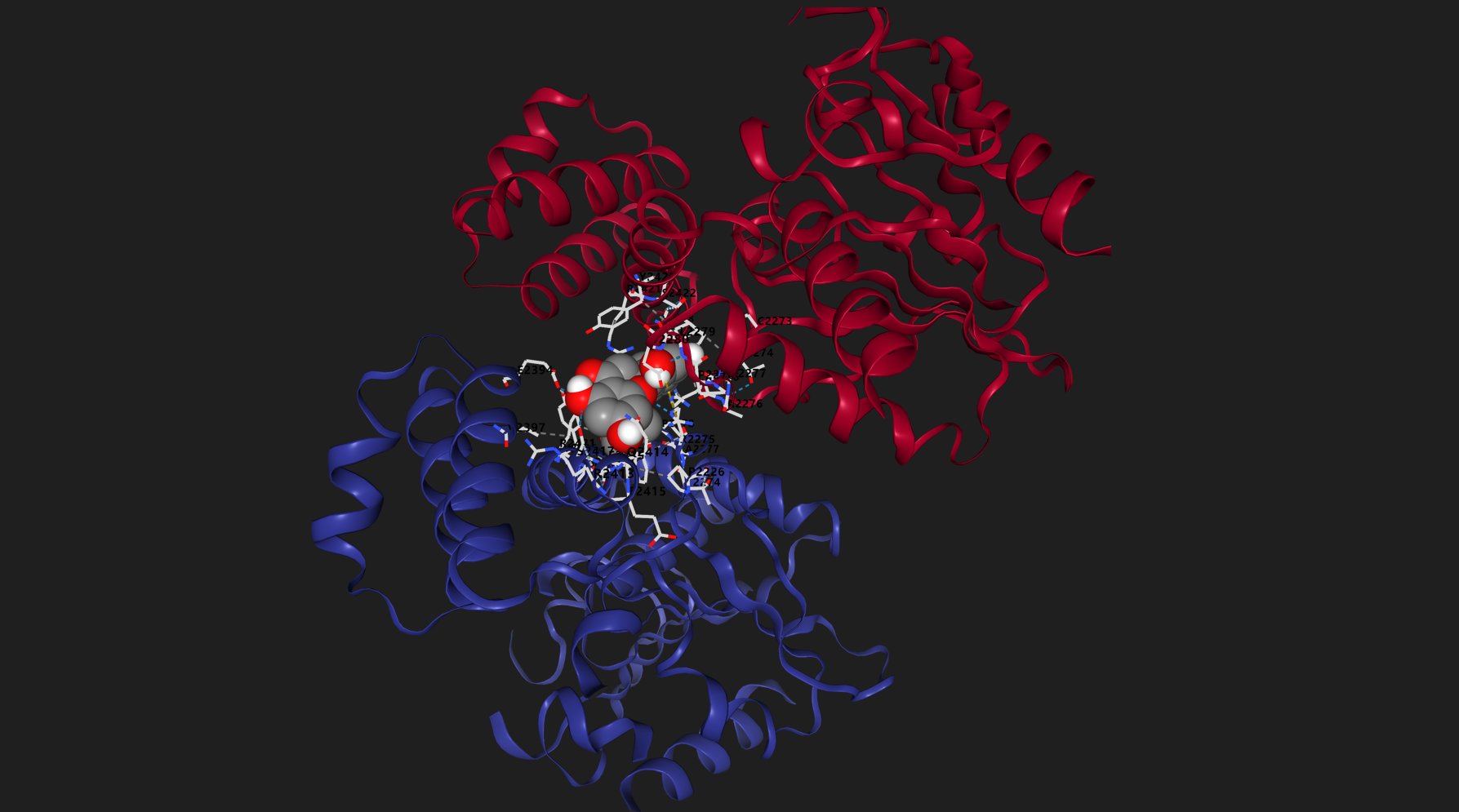Runoff commanding heights Detail decides success or failur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details determine success or failure
优质的客户服务 高效的办事效率

【正如消防体系的核心工作是灭火,防疫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工作应该是应对急性突发传染病。
但在西方长期缺大规模传染病疫情、中国也除2003年SARS之外已经较长时间无重大疫情,防疫系统也就落得个“飞鸟尽,良弓藏”,长期在卫生健康体系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费缺乏,防疫和公卫人员待遇差,防疫梯队缺乏优秀生源而后继乏人。
在目前全社会对于防疫问题及其关切的当下,我们如何建立行之有效、可长期持续的、包括防疫在内的卫生健康体系?
实际上,迄今我国各种意见中,并未提出系统性的建设方案。有些部门甚至将其疫情前的建议原封不动地再度提出,没考虑疫情给人类、给我国提出的严峻的未来安全问题。
需要锁定呼吸系统病毒为主、其他为辅的科学规律,系统思考、全面建立我国包括防疫在内的卫生健康体系。这一体系从教育、医防到行政需要立体化】
我们中国现在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极为关心。以生命至上,促进我国在新的时代将对生命和健康的关心落实到全面审视现有系统,提出行之有效、可长期持续的、包括防疫在内的卫生健康体系。
防疫只在疫情有战时任务,平时不受重视。防疫工作做好了,难以得到肯定,因为就是没有出现疫情。防疫工作做不好,挨批评很容易,属于一般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防疫和公卫体系经费缺乏,防疫和公卫人员待遇差,防疫梯队缺乏优秀生源而后继乏人。
我国现有体系,主导思想欠缺科学基础、国际视野有限、历史发展理解不够。
我国防疫和公卫体系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受到工作不认真、目光短浅和私利障目的影响。
如果不全面系统地改革、构建,可能只是现在大众有一时热情,在疫情过后不出十年,普遍回归原状,即使是20年一次爆发新的重大疫情也难以依赖防疫和公卫体系,国家难以组建有效的团队、长期坚持的梯队、长期有效的机制,而每次全社会伤筋动骨。
我国防疫体系亟需改革
1A) 端正目标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都认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卫生条件的改善、医学科学的进步、疫苗技术的成熟,针对突发恶性传染病的防疫体系重要性下降、甚至可能是过去时。在普遍持有这种观点后,人类在建立健全防疫体系方面、在公共卫生的实践和教育方面,不仅没有用好社会资源和新技术,而是逐步放弃防疫体系,甚至把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的重点转为慢病和非传染病。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也不例外。
重新认识突发传染病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难性,是我国健康和防疫体系的重要任务,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全面端正的态度。
正如消防体系的核心工作永远是灭火一样,防疫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工作也永远是应对急性突发传染病,而其他工作只能是从属。如果颠倒主次,那不是人民所需、国家所要。慢性非传染病,给各个学科很长时间的研究机会,是各个学科可以分担,而无需国家组建防疫和公共卫生体系。
目前全国防疫和公共卫生体系内部不少人自认为是专家,非常反对这一观点。殊不知,这既是防疫和公共卫生的起点,也是今天人类和国家的共识。不能因为防疫和公卫本身在几十年没有重大疫情而出现的转变,当成可以骄傲的经验。那不是经验,而仅仅是经历。
在事实显示突发传染病的危险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可能非常长的时间会存在的情况下,坚持所谓“学科发展”(在公共卫生名义下的诸多领域多发研究论文),而忘记防疫和公共卫生的初心,是错误的。
所以,需要端正态度、纠正目标:急性突发传染病是防疫和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
1B) 医防脱节
我国的卫生健康体系和防疫公卫体系,脱节严重。不仅在行政上长期分开管理,而且防疫人员不能参与医疗体系,医疗体系平时不在防疫一线。
病人一般只知道去医院、当然不会首先去防疫系统,新的突发疾病不会自动向防疫系统报告。需要有机地、密切地结合医疗和防疫体系。
我国的传染病院,归医管局管理,与一般医院一样,而不归防疫体系管理。所以,难免在疫情初期出现传染病院不给防疫体系报警,而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只给上级汇报等情况。防疫体系不能及时得到传染病院的信息,延缓防疫、抗疫。有个不一定有共识的比喻,犹如消防队归自来水公司管理。
1C) 防社脱节
我国的防疫体系,在疫情之前,与社区关系不够紧密。
1D) 人才缺乏
我国的防疫人员、公共卫生人员、传染病医生、社区卫生人员,普遍收入偏低。而工作本身又不是人人趋之若鹜的。这一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导致防疫、公卫、传染普遍人才缺乏,不仅难以招收优秀学生、也难招聘优秀员工,还难以保持现有队伍的优秀人才,因为不断出现的人才流失。
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为什么要学以后周围的人都担心从你身上传染病、而你收入还特别低的专业?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防疫体系出头露面的专家。其实大家想想,过去、现在、将来,自己鼓励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学习传染病、加入卫生力量吗?如果没有,那么,有什么人就是什么人。需要提高质量,就要有长期解决其待遇的方法。
当然有少数人很高尚,但防疫体系不能只依赖少数几个人就能建立。
只要不提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方案,其他方案都会是昙花一现、不可持续。但是,单纯投钱,没有平时工作任务,高薪养无所事事的人,也不可能建立有效的防疫抗疫和公卫体系。
从长远来说,任何口号和说服都无济于事,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案。
呼吸道传染的病毒最危险
未来会有哪些传染病,人类目前无法预计。
但是,我们通过科学理解和对于疫情的了解,可以有共识:对于人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带来最危险疫情的是呼吸系统病毒性传染病。
非典(SARS)和新冠(COVID-2)都是呼吸系统病毒性传染病,并非偶然。
在人类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危害最大的疫情,必然是呼吸系统的病毒传染病。
非传染性的疾病,虽然可以因为发病人数多(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是流行病,但这些疾病都不能造成疫情。
2A) 为什么是病毒?
以前,多种细菌对人类带来巨大危害,但因为医学的发展,例如抗生素,我们已经能够治疗多种细菌性疾病。因为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善,细菌和比细菌大的微生物或病原体感染对人类的危害比以前小很多。少数细菌性疾病,如结核杆菌导致的肺结核,目前还很难根治,我们仍需努力。
因为病毒很小、种类繁多、变异很容易,我们将长期难以治疗所有病毒性感染。虽然我们有针对一些病毒的有效疫苗(例如乙型肝炎疫苗),但是对于很多病毒,我们没有把握很快制造有效疫苗。
2B) 为什么是呼吸系统传染病
非呼吸系统的传染病,传染途径可以避免或者容易切断(血液系统的传染病,如艾滋病,需要体液接触,所以没有个人或使用的生活用具密切接触、没有输血就可以避免;消化系统传染病,没有食入、或者限制排泄物流放渠道,也不会感染)。而呼吸系统可以呼出、吸入,从来是最难以控制的传染途径。
明确呼吸系统病毒性传染病是长期最大的危险,也给我们带来了可以针对性地改革医学教育、医疗和防疫体系。
行政体系的健全和改革
3A) 行政构架
参照我国因为粮食问题而对农业的重视,建立对健康重视的类似行政机制。
我国长期担心粮食,从而建立了一整套促进农业的机制。在我国解决了粮食问题之后,特别是在基本全面小康之后,我们应该根据国情,审视我国发展阶段,从国务院到基层,建立类似对农业重视的整套体系。当然与农业不同的是,日益增长的大量城市对健康日益增加的需求使得城市的健康工作大于农业工作偏向农村的具体方面。
主管的副总理/国务委员领导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国家药监局、国家食品监督局、国家健康研究院(NIHC)。相应每个省也有类似机构。
3B) 疾控中心管理全国传染病
现有CDC是研究院,没有行政职权。
如果合并原卫健委疾病控制局和原CDC,组建新的CDC。赋予全面的、国际通行的CDC管理职能。
原来属于CDC的研究机构不再称为CDC,而改称为“疾控研究院”,除现有几个研究所之外,可以考虑纳入全国其他相关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也可以考虑增加对当地病原的研究和检测。广东和广西等野生动物与人交界处,也可以考虑新设。
3C) 国家健康研究院
从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全面进步、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把保障全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人民对医疗健康日益增长的刚需、中国发展对原创生物医药产业的刚需,是我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是我国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生物医药既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高质量的器械、药物、治疗方法与高质量的健康品质息息相关,最新的药物可以直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寿命。生物医药也是现代高科技的核心支柱之一,生物技术产业是国际增长最快、而我国方兴未艾的产业。在生物医药取得成就,公认可以为一个国家赢得全世界无争议的尊重。我国现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NSFC)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同一数量级,但我国缺乏一个美国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专注医学科学、现经费量近五倍于NSF的机构NIH(国家健康研究院)。英国、法国都有专门医学研究基金会。而人口健康有人群、地域的差别,中国有些常见疾病(如肝炎)并非西方常见疾病,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自主产生中国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对于国家安全、对于提高中华民族健康水平、掌握人类健康主动权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提供人类健康的研究,不仅需要生物医学研究,也需要多学科综合交叉,所以建立NIHC有助于我国健康方向的研究,也有助于促进交叉科学发展。
美国的国家健康研究院(NIH)不仅经费高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而且时间早于NSF几十年。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NNSFC)在美国NSF建立36年后成立,而且当时中国经济状况远不如今天。在美国NIH成立一百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我国全民对于健康非常关心的今天,建立我国的国家健康研究院为时不早。
3D) 医疗管理
国家和各地的卫健委、以及医管局应该只管理医疗,而不对医院和医生提出研究论文的要求。
医学院附属医院对研究有要求,对一部分教授研究有要求,是合理的。但应该由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制定合理的规则。
而不附属于医学院的医院,一般不宜要求医院和医生进行研究。可以在医生有能力和时间的情况下,由医生自主决定。
但是,很多地方的卫健委和医管局因为医院排名等因素,要求一般医院及其医生有研究、有论文。这种做法不合适。它经常适得其反,不仅低劣论文直接影响诚信,而且影响医生对病人的服务工作。
卫健委和医管局应该集中精力管理医疗,不宜越位管理科学研究。
3E) 医学院与附属医院的关系
全世界的医学院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
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相得益彰。医学院需要有教学医院,医学院的教授、研究、交流、合作可以促进医疗质量的改善。
高质量的医生,如果只关心医疗,无需到附属医院工作。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附属医院的医生,收入不如少数独立行医、只行医不教学科研的人。
高质量的医生,到附属医院工作,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不愿意只做医疗服务,而不做教学和科研。他们中的多数希望做对世界有影响的科学家、教书育人的教授。
所以,一般来说,附属医院质量都高于非附属医院、高于独立行医执业者。
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除了学制,绝大多数都是承接了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但是,美国早已解决的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关系问题,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妥当的解决。
美国的附属医院,不仅由医学院任命其关键岗位、决定教授系列职称,而且给医学院付费。没有清晰合约的,不能成为附属医院。保证了医学院对医院的领导,也保证了医学院与附属医院的互惠关系。
如果医院不愿意附属于医学院,可以独立。独立的医院认为自己有教学能力的,也可以像有些国家建立附属于医院的医学院。
通过比较,证明是医学院领导附属医院的效果好,还是医院领导附属医学院的效果更好。
建立长期稳定和良好的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关系,在中国需要从上而下的体制建设。
防疫体系改革
监控突发传染病的关口应该前移,可以考虑移到全国每一所医院和社区。
4A)CDC管理全国防疫站、传染病院和一般医院的“整合卫生科”
除现有的防疫系统之外,CDC的管理部门应该垂直管理全国每一个传染病院。而一般医院应该有一位副院长有CDC任命,对CDC负责,每天上CDC的提供信息。有传染科、重症医学科、发热科的非传染病院,其科主任由该副院长提名,CDC和医院双重任命。这些科主任每天向副院长报告情况。
非传染病的医院普遍设立“整合卫生科”,将经过预防医学培训的临床医学人才,融合到医院,以适应“平时”(无疫情期间)和“战时”(有疫情期间)的工作需要。因为今后长期的烈性传染病绝大多数应该是病毒,其检测主要依赖核酸检测;而平时医院面临的重要疾病也需要通过核酸有关技术进行诊断、检测和治疗。在医院新设立的”整合卫生科”,处于“战时”(防疫)阶段时,可开展病毒监测、为疾控一线做贡献。在“平时”(日常工作阶段)可开展基因监测、临床试验、临床科研,为医院的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和科研统计提供帮助。这样,既解决了医院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把疾控第一线前置,解决目前CDC系统与医院的脱节、从而CDC得不到最前沿的信息问题。“整合卫生科”因同时掌握大数据,对医院的科研整合、研究水平的提升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对于大医院,建立传染病监测,应该容易接受。小医院为什么也要监测?小医院是否应该给病人看小病为主?在没有疫情可能的情况下,当然小医院主要是给病人看小病。但是,在有疫情影响全国、影响全人类的情况下,小医院也应该加入监测传染病的第一线,因为它们实际就在接触病人的第一线。
4B)社区核酸监控
社区应该进行核酸检测。除了大家熟悉的监测病毒,还可以监测一些常见疾病。
检测哪些序列、什么时间间隔、如何空间分布等,都需要科学研究和探索。
因为病毒监测是核酸检测,而慢性病基因分析也是核酸分析。所以,“穷病”可以与常见病、“富病”一道由同一批人检测。这样,在疫情不流行的平时,用常见病和富病的支出养了穷病突发所必需的人员。也用平时的工作保持了战时的基本技术。
通过类似4A和4B的体系建立,才能“平战结合”、“穷富联通”。
公共卫生教育改革
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学院,包括美国的、中国的,都是应对传染病导致的疫情而建立。
但是,在发达国家的疫情大大减少后,公共卫生学院被迫寻找没有疫情时候的出路。
美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带头建立了多个专业。据于公共卫生学院传统的统计学和流行病学优势,美国(和后来的中国)公共卫生学院都涵盖了多个学科,包括以统计和流行病等学科提供的技术,研究重大慢性病,从癌症、代谢疾病、到精神疾病。这些与时俱进的发展,非常必需。
与时俱进后,大多数公共卫生学院的核心力量是慢性疾病的基因分析、毒理学等容易平时出论文的专业方向。
但是,必需坚持防疫抗疫是公共卫生学院存在的根本理由,培养学生的根本目标。如果人类永远没有疫情,应该可以大规模减少公共卫生学院的规模。只需要统计系、流行病学系、环境卫生系。其他工作,都可以是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癌症医生)、专门研究科学家(人类遗传学家、基因组学家)请统计和流行病专家协助、合作,而无需专门设立庞大的公共卫生学院。
设立专门的公共卫生学院,目的永远是防疫抗疫。但因为很可能长期没有疫情,平时如何发挥公共卫生学院和公共卫生人才的作用,维持其战斗力,就是非常大的问题。
全科医学的学习阶段也将加强分子生物学、病毒学、流行病和统计培训。全科医生在社区的日常工作也将扩展到核酸分析监测病毒和常见病的基因分析。其技术的提高将为社区人民提供更全面、优质的服务,也就可以有合理收入,这样就增强了全科医师岗位的吸引力,有利于社群和全科医生双赢结构的建立。
医学教育改革
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体系,是国外引进的。早期有欧、日、美等模式,最后主要是美国模式。这一医学教育体系,有非常合理的成分,所以被广为采纳。
但是,原模式在美国就有发展、改进,而在我国现阶段,明显可以提出深刻改革的模式。二十世纪之前,美国医学教育体系混乱、质量较差。卡内基基金会请犹太裔教育家Abraham Flexner(弗勒克斯纳,1866-1959)调研当时美国的全部医学院后,于1910年提出《弗莱克斯纳报告》(美国和加拿大医学教育)。
这一报告的理念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助,推动了美国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建立了美国医学教育的体系、提高了美国医学教育的质量。但它也一直有一些需要与时俱进的问题,不可能它的全部内容都适合所有时间和地点。例如,它的八年制要求,有减少医生、便于医院和医生垄断医疗市场的问题。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越来越昂贵,与整套医疗体系、包括医学教育的故意高度精英化有关。
我们应该根据时代、根据中国情况,改革我国的医学教育。
6A)六年制临床医生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反复证明,六年制的医学教育,完全可以胜任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所以,培养医生,完全不应该追求博士学位,而应该追求实际效果,在合理的年代、合理的成本,得到合格的医生。增加医生培养的年代,势必增加国家和个人的资源投入,最后成本不可能都消化,而会有部分转移到病人身上。
为了能够参与未来的疫情防控,临床医生培养过程需要加强分子生物学、病毒学、传染病、流行病的教学,以便应急之需。
医院不能追求学历年限越高越好。应该根据为病人、为社区、为国家服务而有合适比例的不同医学教育背景的人才。
6B)十年制医学科学家
我国完全没有必要追随美国的一个历史遗迹,培养所谓八年制的医生。绝大多数在国内主张推行MD/PhD的行政和教学人员,并无切身体会,而冒着隔靴搔痒、如果不是东施效颦的危险。八年制培养的临床医生,比六年制好不了多少,而对于培养同时能够从事医生和研究的医学科学家又时间不够。
美国的MD/PhD实际是4年本科加6年医学和研究,是十年制。而初期很受热捧的MD/PhD到现在也并非得到一致的推崇。我第一次任教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曾是美国MD/PhD最多的学校,我自己的就带过MD/PhD的学生。这批学生分化很大。虽然早期目标是双栖,但后来实践的结果是大量分化为只从事医学或只从事研究。我国如果坚持培养医学科学家,恐怕没有十年就给博士,效果有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八年制的医疗、研究两不靠学生。我们应该坚持大部分医生就是医生,六年制医学培养就可以。我们可以有少部分是十年制的医学科学家。
医院招聘、晋升、医院领导的选拔都应该是按需,而不是按学历长短。
目前,即使最好的医院,包括协和医院,大部分医生的研究时间和研究水平都不够,这不是因为医生个人有问题,而是精益求精的医术培养与长期钻研的医学科研在时间上有根本的冲突。
应该承认事实,医疗为主的医生和研究为主的医生有一定比例,各司其职,而不是一味强调好的医生都要做研究。选拔医学院或医院领导不能个个都要求研究论文。
这些体制上的问题解决后,六年制医生与十年制医学科学家安分守己,各自发挥利国利民的作用。
6C)调整和改变基础医学本科教育的目标
中国医学院普遍有基础医学院,而且招收本科学生。这是今天国外医学院普遍没有的部分。
基础医学院招生的历史原因是培养医学院的师资。今天,这一历史任务早已完成,而且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基本不可能成为师资,而常常沦为老师的劳力。
以前基础医学学院学生的培养目标:基础医学的师资和研究人员,应该全部由基础医学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所替代。
需要彻底改变基础医学院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和学制。应该都只能是四年制,毕业后成为研究生,或者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在我国方心未艾的生物医药产业逐渐起飞、走上正轨的时代,投入生物医药产业。
6D)药学院以药物研发和生产为目标职业
美国的药学院以培养药房的药剂师为主要目标。这对于我国没有借鉴性。事实上,在已经有医生开处方,而每一个处方药有明确文字说明的情况下,普遍加上大量的药房药剂师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提高社会成本。一个药剂师应该可以管理很大的药房,很多的技术员,而不用个个都必需药学院文凭。
而药物创新、研发、制造、验证、监管,需要大批人才。药学院本科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可以加入以上各个环节的人。
如果普遍这样设立药学院、药学系,为我国药物发展可能提供其他国家没有的、独特而适用的人才,为本世纪我国药物工业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而打好坚实的基础。
6E)生物医学工程以仪器研发和生产为目标职业
美国的生物医学工程与其他学科有重叠。例如,美国有一部分很好的生物医学工程系,内含相当一部分用电生理和物理学工具研究神经科学的研究人员。这无异于扩大神经科学系。
中国设立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不少。但不能简单模仿美国,例如就不应该涵盖神经科学,因为中国也在所有医学院都已经有神经科学系。
中国的生物医学工程院系,应该以医学仪器的研发和生产,为培养学生的职业目标。在这一目标下,老师及其研究可以更宽泛、包括一部分基础,而并非每一个老师、每一个课题组都在研究仪器。
6F)医学教育管理
中国的教育体制,将医学教育纳入教育部体系后,对医学教育没有稳定的管理体制。
医学教育方向、模式、评价不时出现为医学界所诟病的一些问题,有些成为老生常谈,经久不改。
目前医学教育管理,人治的随意性比较大。有时有懂一些医学的人员在高层管理,有时出现懂医学的在教育部最高职位只是副处长。
医学教育界和医疗界经常认为医学专家在教育系统缺乏话语权,医学教育政策出现明显外行和不妥也没有合适的反馈渠道,得不到有效处理。
教育部应该设立医学教育司,成为常设的机构,由懂医学和医学教育的人组成,在医学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专门统筹全国医学教育,制定和监督执行能够相对稳定的政策。
本文来源于饶毅教授发表在《饶议科学》和《知识分子 》
原文连接:https://mp.weixin.qq.com/s/aFF52oKeZxtbtobNz8fa8g
Copyright © 2021-2025,www.tuohuangniu.tech,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 © 拓荒牛科技 未经许可 严禁复制 建议使用1366X768分辨率浏览本站
渝公网安备:50022702000893号
公司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铁山路1号附5号203-1室